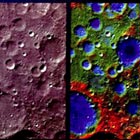廬山會議之后,,一次飯畢,,彭老總要與父親談?wù)?。因餐廳的另一半是用屏風(fēng)隔開的會議室,,他們就轉(zhuǎn)過去談,。我在飯桌上“打掃戰(zhàn)場”,,看到楊爸爸站在屏風(fēng)這邊側(cè)耳傾聽,。彭伯伯說話的聲音大而急,,滿口湖南腔,,我一句也聽不懂。忽然,,他厲聲高喊了一聲:“尚昆,,你也過來!”我嚇得屁滾尿流,,撒腿就跑,。這場景,如今仍歷歷在目,,而紅三軍團(tuán)三位巨頭戰(zhàn)友之間的交談,,一個孩子即使在場細(xì)聽,也肯定絕難理解,。
“文化大革命”前夕,,楊爸爸和羅瑞卿叔叔、彭真叔叔,、陸定一叔叔首當(dāng)其沖,,第一批被打倒,。據(jù)說楊爸爸的錯誤是私錄毛主席和常委的講話,還和羅瑞卿等人一起積極參與反黨活動,。我敢說,,聞?wù)吣患{悶,既不可想象,,更無法理喻,,但那年頭,就那么怪,,大家也就那么“信”了,!1966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大西門打籃球,,透過賽場觀眾,,看見妞妞跟著一輛滿載家具的卡車緩行,一副“已是黃昏獨(dú)自愁”的樣子,,迎著夕陽,,垂頭走到門口,登車而去,。在場的人們議論,,說楊家搬出去了。我心里感到異樣:兩小無猜,、一塊兒長大,,臨走也沒來得及說句什么。說實(shí)在的,,就是放在今天,,她若真的來告別,我又能說什么呢,?
直到1967年4月,,在清華大學(xué)十萬人批斗大會上,我才又遠(yuǎn)遠(yuǎn)地見了一眼楊爸爸……不久,,又見到妞妞,,自是悲喜交集。那時,,和平里東有座五號樓,,是著名的“黑幫樓”。我們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會的關(guān)注,,不分白天黑夜,就來個“突然襲擊”“查戶口”,。我們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櫥架子上,,或蹬窗上樓頂,小時候在軍隊(duì)里學(xué)會的隱蔽,、攀登,、越野本領(lǐng)都派上用場,練到爐火純青,。
1968年年底,,又巧了,,妞妞和我被同時分配下鄉(xiāng),,而兩個學(xué)校又安排在同一個縣。我算被“勞改”,,她雖是插隊(duì)知青,,也屬被監(jiān)督之列。我們用雞毛信方式,,打密語暗號,,約定時間地點(diǎn),溜出幾十里相會,。坐在白楊樹林間的草地上,、渠墚邊,天南地北地聊,,追憶似水年華,,共抒對親人的思念。聊到盡興,,寵辱皆忘……現(xiàn)在想起,,還挺浪漫。六年后楊爸爸被“解除監(jiān)護(hù)”,,下放山西“接受審查”,。妞妞去陪伴,走了,。我雖更孤獨(dú),、更寂寞,心底卻真為她高興:總算能與父母在一起啦,。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楊爸爸回到北京。我去看望,,他顯老了些,,瘦了許多,比過去嚴(yán)肅了,,然而目光炯炯有神,,仍是那么有親和力,。不久,我母親也出獄了,。
以后二十年間,,不定期的,楊爸爸總惦記著請我們?nèi)フ務(wù)?。開始,,他和媽媽談當(dāng)年與父親相處的許多事,而媽媽又因我是學(xué)歷史的,,讓我作陪旁聽,。日久了,楊爸爸一見我,,也愛回憶往事,。他記憶力非凡,黨史軍史上有許多謎團(tuán)疑案,,搞不清原委,,他幾乎全能講得一清二楚。當(dāng)然,,也有例外,。有一次,他忽然問我:“你說說,,為什么毛主席晚年要打倒你爸爸,?”我可真哭笑不得,回答說:“您與毛劉是長期的老戰(zhàn)友了,,怎么問我呢,?我每次見您都想問這個問題,一直沒好意思開口,?!彼烈髁季茫ь^自語道:“想不透哇,,想不透,!”幾乎完全一樣的問題和場景,也出現(xiàn)在彭真叔叔與我的談話中,。說實(shí)在的,,他們那一代生死至交都百思不解,后世之人就只有枉猜妄評,,恐怕永久也難想透了,。
|
編輯:
胡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