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帶9歲女兒練攤,討到公道又如何,?

瓜農(nóng)式小販,、社長式小販、學(xué)生式小販,,當(dāng)他們各自與城管式執(zhí)法發(fā)生沖突時,,即便他們反抗程度一樣、身心或皮肉受傷害程度一樣,,但受眾同情心會因角色不同而持不同的態(tài)度。這是一個按身份站隊的時代,,不是以法理站隊的時代,。
劉雪松 鳳凰評論特約評論員
與“暴力執(zhí)法”相關(guān)的輿論,在中國有一種同仇敵愾的味道,。但“父親帶9歲女兒練攤”這次,,顯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分裂。
輿論分裂,,與暴力沖突的執(zhí)法一方,,究竟是城管隊員、還是綜治辦人員的區(qū)別無關(guān),,與究竟是執(zhí)法人員先動手,、還是練攤的父親先動手,也沒有多大關(guān)系,。卻與這位父親的身份有關(guān),。并且,由這位當(dāng)事人的特殊身份,,讓一個特殊的新詞廣為傳播——新聞碰瓷,。
追究“什剎海練攤”誰先動手,是一個做無用功的過程,。這種技術(shù)層面的事,,如果拿來判斷整個事件的是是非非,就將一個嚴(yán)肅的社會管理命題,淪為一地雞毛的街頭打斗,。而事實上,,執(zhí)法暴力泛濫,并不是由拳頭大小決定,、而是由權(quán)力大小決定的,。
這起新聞事件的主人公,其實有兩位,。一位是父親,,一位是9歲的女兒。前者最初在輿論中出現(xiàn)的身份是“北京一雜志社副社長田先生”,,后來的身份被臆想并傳播成“新京報田姓副總編”,。等到這些身份回到“某民族書畫雜志社副社長田予冬”時,這個人物,,已經(jīng)在公眾的印象中,,以概念化的思維方式,判斷出具有著運作“新聞碰瓷”的特殊背景,。
這與瓜農(nóng)之類的小攤小販,,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田予冬明知在什剎海這樣的風(fēng)景名勝區(qū)練攤違法,,還要帶著9歲的女兒去試法,這在許多受眾眼里,,便不再是養(yǎng)家糊口謀生計的弱勢群體,,而是有著“得瑟”的意味。
許多人寧愿為一個真正的小販被毆而拼命與官方死磕,,并且不論前因后果誰對誰錯,,也不愿為一個以“孩子社會實踐”為理由、卻有著權(quán)力背景的人說一句好話,。
這是一種撕裂的感覺,,一種超越于事件本身的分裂情緒。它與這場輿論分裂的另一方表態(tài)的諸如“堂堂北京為何容不下一個9歲孩子社會實踐的地攤”,、“別讓暴力侵入孩子的心靈”等煽情之詞一樣,,都是一種緣自表象的情緒宣泄。
瓜農(nóng)式小販,、社長式小販,、學(xué)生式小販,當(dāng)他們各自與城管式執(zhí)法發(fā)生沖突時,,即便他們反抗程度一樣,、身心或皮肉受傷害程度一樣,但受眾的同情心,會因為社會角色的不同而持不同的態(tài)度,。這是一個按身份站隊的時代,,不是以法理站隊的時代。社長式小販,,此次如果不是與學(xué)生式小販捆綁在一起,,可能田予冬強調(diào)自己的這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很難在以往一邊倒的仇恨城管情緒中,,找到堅強的支持者,。這便是“什剎海練攤事件”真正具有標(biāo)本意義的新聞價值所在。
但是,,輿論分裂,,并不代表人們要么站在了練攤的父親與他的女兒一邊,要么站在了執(zhí)法部門一邊,。按習(xí)慣性的一邊倒情緒,,城市管理執(zhí)法部門這桿大旗下,估計除了類似于武漢那位做了7年小販生存依然艱難,、最后被城管收編了去的,,一般情況下,民意的隊伍,,城管輪空的可能性比較大,。眼下,為屢曝暴力執(zhí)法的這支隊伍公開相挺者,,不僅需要城管般不懼良知的勇氣,還需要有不畏世人唾罵的胸懷,。這種境界,,很少有人做得到。
所以,,圍繞“什剎海練攤”的輿論分裂,,是一次典型的身份認同的情緒性站隊。這支隊伍,,只有權(quán)力與平民之分,。“副社長田予冬”,,同樣像站隊被輪空了的城市管理執(zhí)法隊伍一樣,,被置于一個強勢的權(quán)力、與另一個強勢的權(quán)力相抵銷的尷尬處境,。表面上看,,很多人在支持“田副社長”,其實是在力挺他9歲的女兒。人們找到了“學(xué)生社會實踐”這個容易引起情緒共鳴的敏感點的同時,,也找到了宣泄對城市管理執(zhí)法長期積蓄的“民憤情緒”的反攻軟肋,。許多陰謀論者以觀察家的姿態(tài),將其歸結(jié)于所謂的南方系北方系的站隊,,便難免落入悲情與矯情,。
追究“什剎海練攤”誰先動手,是一個做無用功的過程,。這種技術(shù)層面的事,,如果拿來判斷整個事件的是是非非,就將一個嚴(yán)肅的社會管理命題,,淪為一地雞毛的街頭打斗,。唾沫浪費在這上面,最多只能判斷毆斗過程中誰先發(fā)制人,。而事實上,,執(zhí)法暴力泛濫,并不是由拳頭大小決定,、而是由權(quán)力大小決定的,。
同樣,即便涉事的執(zhí)法人員,,真做到了“先對孩子說聲對不起”,,也不可能解決暴力執(zhí)法對社會和法治的傷害。如果要對這個9歲的孩子說聲對不起,,那么,,這支粗暴的執(zhí)法隊伍,早就應(yīng)該向發(fā)生在中國的,、目擊打死打傷小攤小販的所有孩子說聲對不起,,對所有受到傷害的小攤小販的未成年后代說聲對不起。他們欠下的法治債,、感情債,,不只什剎海練攤的9齡童這一個。他們欠下的,,是整個社會,。
但是,“副社長田予冬”,,無法為這場“債務(wù)運動”擔(dān)當(dāng)清算者,、或者打抱不平的角色。人們反而在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種帶有身份和權(quán)力色彩的,、與城市管理執(zhí)法所表現(xiàn)出來的“不合作”情緒,。這是許多圍觀者,讓城管大旗輪空,、又讓“副社長田予冬”揭竿反抗旗幟同時輪空的特殊心態(tài),。這種微妙的關(guān)系在于,人們渴望具有一巴掌能夠搞得定局面的權(quán)力去制服暴力執(zhí)法,,卻不愿見到帶有權(quán)力色彩的力量,,用戲碰的心態(tài)去展示對暴力執(zhí)法的肌肉。這就是“副社長田予冬”被指稱“新聞碰瓷”之后辯解不清的尷尬所在,,也是這起事件所表現(xiàn)出來的民眾“凡權(quán)力不合作”的時代性格,。
與權(quán)力的不合作,是對法治缺失的一種情緒叛逆,,也是對城市管理中暴力執(zhí)法久而不治的情緒抵抗,。不明確限定暴力執(zhí)法屬于一刀切式的違法紅線,而用細碎的法則去界定附著在類似事件身上的細節(jié)是否合法,,這是一種本末倒置,。
暴力執(zhí)法,是執(zhí)法犯法,。這種情形下,,再公平公正的法,也會被弄成惡法,。惡法非法,,不如無法。如果城市管理中的惡法行為可以司空見慣,,那么,,惡法對于民眾的一次次傷害,就會成為這支所向披靡的隊伍,,向民眾敲個不停的一聲聲喪鐘,;人們與城市管理執(zhí)法隊伍之間的那種撕裂帶來的疼痛感,便會蔓延到權(quán)力與民眾之間,。
要么被惡法劈頭一個巴掌,要么讓劈頭一個巴掌就能擺平惡法猖獗的權(quán)力驚醒,。前提是,,那些倒在暴力執(zhí)法拳腳之下的生命、那些撕裂般的痛楚,,能夠成為民眾叩響權(quán)力大門的聲音,,成為足以喚醒權(quán)力的警鐘。
一個巴掌拍不醒,。那么多諸如瓜農(nóng)這樣的生命都拍不醒,,“副社長田冬予”這雙客串之手,,實在顯得書生氣了些。即便為9歲的女兒討到個公道,,那也不是真正的公道,。 轉(zhuǎn)載請注明出處


吳虹飛案:司法機關(guān)分得清違法和犯罪
司法機關(guān)懂得平衡公民言論自由權(quán)與保障社會秩序之間的關(guān)系,也分得清普通違法與犯罪的區(qū)別,。[詳細]
帶女兒練攤 討到公道又如何,?
他們欠下的法治債,、感情債,不只什剎海練攤的9齡童這一個,。他們欠下的,,是整個社會。這是一個按身份站隊的時代,,不是以法理站隊的時代,。[詳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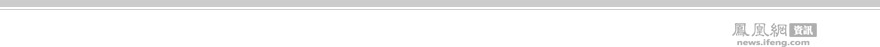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wǎng)友意見,鳳凰網(wǎng)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