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缺乏現(xiàn)代技術(shù)支持的情況下,,傳統(tǒng)帝國(guó)是如何實(shí)現(xiàn)對(duì)山城的有效控制的呢?物質(zhì)資源匱乏,、教化程度偏低的山城又是如何應(yīng)對(duì)帝國(guó)權(quán)力的呢?山城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史視野下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2016年4月1日下午,,由臺(tái)灣大學(xué)上古秦漢史讀書會(huì)、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huì)工作坊主辦的“帝國(guó),、邊疆,、山城——區(qū)域史研究座談會(huì)”在臺(tái)灣大學(xué)文學(xué)院歷史系會(huì)議室舉辦。會(huì)議由臺(tái)灣大學(xué)歷史系助理教授閻鴻中老師主持,,德國(guó)圖賓根大學(xué)漢學(xué)系副教授黃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助研究員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yǔ)言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游逸飛,、臺(tái)大人類系兼任助理教授黃川田修四位青年學(xué)者做專題演講,。
在區(qū)域史研究框架更趨細(xì)膩、歷史學(xué)研究提倡多學(xué)科交叉的背景下,,他們運(yùn)用方志,、碑刻、族譜,、簡(jiǎn)牘,、考古遺存等不同的史料,探討了四個(gè)中國(guó)歷史上的深山小城在選址,、資源,、交通、軍政,、歷史認(rèn)同,、族群互動(dòng)等領(lǐng)域產(chǎn)生的問題,。
“山城”作為一種帝國(guó)邊疆,與傳統(tǒng)意義上和鄰國(guó)接壤,、由帝國(guó)新近開發(fā)拓殖的“邊境地區(qū)”有一定的區(qū)別,。它們?cè)诘乩砩喜灰欢ㄟh(yuǎn)離政治核心區(qū),卻因?yàn)榻煌l件的局限使得它們與世隔絕,。在缺乏現(xiàn)代技術(shù)支持的情況下,,傳統(tǒng)帝國(guó)是如何實(shí)現(xiàn)對(duì)山城的有效控制的呢?物質(zhì)資源匱乏,、教化程度偏低的山城又是如何應(yīng)對(duì)帝國(guó)權(quán)力的呢,?山城研究的特殊性及其在全球史視野下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而“邊緣”轉(zhuǎn)而影響“中心”的研究角度,,也是傳統(tǒng)中國(guó)史研究沒有充分挖掘的,,由邊地山城的建制、運(yùn)作來討論帝國(guó)中心的發(fā)展動(dòng)態(tài),,正是這樣的一種嘗試,。方志、譜牒等史料側(cè)重反映基層社會(huì)史變遷,,田野調(diào)查的研究方法則讓研究者深入民間,,與會(huì)的幾位年輕學(xué)者無論從研究的題材還是方法上,都頗為前沿,。
黃菲:明清東川府地景改造中隨意而為的風(fēng)水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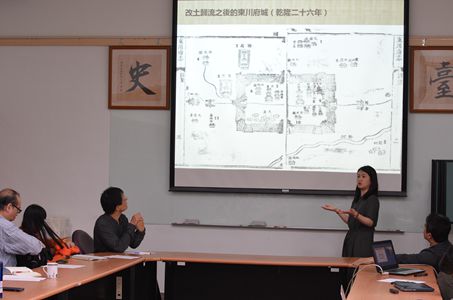
(德國(guó)圖賓根大學(xué)漢學(xué)系副教授黃菲報(bào)告東川縣景觀)
首先作發(fā)言的是黃菲,,她研究的是明清時(shí)期云南東川府的地景改造問題。東川府位于昆明市東北部,,是彝族六祖分支的所在地,。它長(zhǎng)期不在帝國(guó)的直接統(tǒng)治范圍內(nèi),明中后期仍由當(dāng)?shù)氐牡撌贤了具M(jìn)行管理,。至雍正四年(1726)改土歸流,,它被歸入云南省,帝國(guó)的力量才逐漸進(jìn)入,。乾隆三年(1738),,清朝在此開采銅礦,考慮建城事宜,。最先參與計(jì)劃的官員崔乃鏞認(rèn)為,,要在這個(gè)被認(rèn)為是“東故夷獠窟”的地方建立新城,就要舍棄原本的土司駐地,,另辟新址,。由于滇東北時(shí)常面臨沼澤擴(kuò)張、洪水泛濫水的問題,,新城被選址在了一個(gè)半坡上,。根據(jù)崔乃鏞的風(fēng)水知識(shí),,城池要分成上下半城,所有比較重要的官方建筑都被規(guī)劃在了山坡上,,以彰顯天朝權(quán)威,,而民居、廟宇則應(yīng)放在下半城,。有趣的是,,城池規(guī)劃大功告成之后,崔乃鏞就被遣調(diào)至他處了,,繼任的王至,、饒夢(mèng)銘兩位官員完全沒有落實(shí)前任的規(guī)劃,而將官府,、管理銅政的機(jī)構(gòu)都設(shè)在了山下平地處,,而將萬壽宮、商業(yè)會(huì)館等民間設(shè)施建在了來往不便的半山腰,。這說明帝國(guó)在邊陲城鎮(zhèn)的地景設(shè)置上并沒有固定的模式,,天高皇帝遠(yuǎn),東川又不同于京,、杭這些有傳統(tǒng)城建基礎(chǔ)的古都,,建立新城的風(fēng)水講究往往依從于官員個(gè)人的喜好,有很大的發(fā)揮空間,。
在東川府的地景布置上,另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強(qiáng)烈的軍政色彩和雜糅的民族分布,。雍正八年(1730)崔乃鏞平定當(dāng)?shù)赝了九褋y,,請(qǐng)示時(shí)任云南巡撫的鄂爾泰有關(guān)建城的風(fēng)水知識(shí),卻得到了與當(dāng)?shù)仫L(fēng)水師率先處理土地分配不均,、緩和階層沖突的主張完全相反的命令:加固軍事要塞,,重視邊城在平定叛亂時(shí)的應(yīng)對(duì)能力。因此才建成了后來規(guī)模更小,、布局更加緊湊的東川府城,。在城內(nèi)的田地分布上,多元民族互相交融,、漢人彝人比鄰而居的情況也很普遍,,可見嚴(yán)格的民族隔離政策并沒有在南方邊區(qū)有效開展,清朝在保護(hù)滿漢等主要民族權(quán)益,、維護(hù)民族關(guān)系內(nèi)部平衡等問題上并不著意,,只要求這個(gè)“蠻夷之邦”能夠維持銅礦運(yùn)輸和政治平穩(wěn)就好。東川府有壯麗的紅土風(fēng)貌,,由中國(guó)傳統(tǒng)文人風(fēng)景模式演變而來的“東川十景”,,也幾乎設(shè)立在銅運(yùn)沿線,。東川府在鎮(zhèn)邊、采礦上的單一城市定位,,由它被納入帝國(guó)統(tǒng)治而得到進(jìn)一步的強(qiáng)化,。
李仁淵:福建屏南縣的文明改造中帝國(guó)如何在場(chǎng)
接下來報(bào)告的是曾翻譯羅威廉(WilliamRowe)《中國(guó)最后的帝國(guó):大清王朝》一書的李仁淵。他以福建屏南縣為研究中心,,把這座清朝雍正時(shí)才建立的新縣城中帝國(guó)力量的滲透過程做了前后梳理,。屏南地區(qū)深居福建內(nèi)陸,本隸屬于古田縣,。此處山多地少,,村莊沿河而建,規(guī)模非常有限,。它的人群變動(dòng)也很大,,人口遷移性強(qiáng),在明代就經(jīng)歷了復(fù)雜的社會(huì)變動(dòng),,文明開化程度很低,,官方稱之為“夫比匿兇人,結(jié)納無賴,,非以強(qiáng)食弱,,便以大欺小”。雍正十二年(1734),,為加強(qiáng)對(duì)福建東南山區(qū)的控制,,清朝開始在古田縣細(xì)劃行政區(qū),但因交通不便,,駐扎官員始終沒有進(jìn)入屏南地區(qū),。乾隆元年(1726),首位清朝官員沈鍾赴任屏南,。他在《屏南縣志》中這樣描述初來的情形:“每夜猛虎聚于墻外,,人煙寥寥不過四五十矣。”盡管有所夸張,,但荒蠻程度可以不難想見,。
屏南縣的改造是以科舉為核心、培植地方士紳的過程,。沈鍾首先開放了屏南的考試名額,,用以培養(yǎng)官府可以動(dòng)員的生員力量,并藉此團(tuán)結(jié)地方勢(shì)力,。從他的生員分布來看,,基本均攤給了附近的地方大族勢(shì)力。此后,他又以“本地籍貫”,、“寄屏人士”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解決了古田、屏南童生考試爭(zhēng)奪籍貫的問題,。此舉成為他日后遭致地方勢(shì)力排擠的導(dǎo)火索,。盡管沈鍾最后因沒有處理好官府與地方的關(guān)系被彈劾罷官(以致他窮困潦倒、客死他鄉(xiāng)),,但是興科舉,、重教化的風(fēng)氣卻在此地保留下來,并成為帝國(guó)與山區(qū)維持連結(jié)的唯一紐帶,。如地方實(shí)力派張步齊通過與官方的合作,,在福建內(nèi)陸販賣食鹽起家,迅速崛起,,繼而修建祠堂,、繕寫族譜,成為一方縉紳,。這一“文明化”過程與南方諸省,,尤其是清代在臺(tái)灣的開發(fā)有許多類似之處。報(bào)告人李仁淵指出,,通過比較清朝勢(shì)力進(jìn)入前后,,地方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階層分布,、歷史認(rèn)同,、記憶型塑等問題,可以清楚地看到國(guó)家是如何產(chǎn)生影響力,、如何在一個(gè)邊遠(yuǎn)山城實(shí)現(xiàn)在場(chǎng)(atpresence)的,。官方與地方勢(shì)力的你來我往權(quán)利互動(dòng),亦有較為普遍的價(jià)值,。
帝國(guó)以科舉影響邊陲的代表性與內(nèi)在限度
筆者認(rèn)為,,屏南縣這座“山里面的新村莊”,,是康雍以來人口激增大背景下,,南方各地山區(qū)移民墾殖的縮影。屏南縣以科舉為核心的改造,,是帝國(guó)在傳統(tǒng)地區(qū)團(tuán)結(jié)現(xiàn)成的士紳階層,、在新開擴(kuò)地區(qū)培養(yǎng)新的士紳勢(shì)力以維持儒教型國(guó)家的基層統(tǒng)治的典型手段。其中所產(chǎn)生的暴亂頻發(fā),、官弱民強(qiáng)等問題,,亦不過是這種進(jìn)度緩慢的間接統(tǒng)治建立之初所必然遭遇的情況。

(臺(tái)大歷史系教授,、臺(tái)灣史著名學(xué)者李文良 沈雪晨攝)
兩場(chǎng)報(bào)告之后,,臺(tái)大歷史系教授李文良等老師提出了這樣的疑問:難道沈鍾之前,,屏南地區(qū)完全沒有官方的影響?以科舉的進(jìn)入與否來衡量是否過于單一了些,?李仁淵回到道:現(xiàn)有的史料基本是清朝進(jìn)入以后官方所修的方志,,以及各大家族進(jìn)入文明開化以后自己為自己編的族譜,僅從文字材料記載上看,,科舉的興辦確實(shí)在邊區(qū)開發(fā)中起到了關(guān)鍵的作用,。另外,所有做族譜的人都知道它們一追溯祖先就順接到炎黃堯舜顯然是無中生有,,但族譜何時(shí)開始出現(xiàn)亂接祖先的現(xiàn)象仍然重要,。它顯示了一種文化資源在何時(shí)得以產(chǎn)生,它既有外來的華夏文明認(rèn)同,,也有內(nèi)部家族發(fā)展壯大的需求,,兩者只有結(jié)合起來,才形成了一個(gè)完整的族譜敘事,。并且在細(xì)節(jié)的操作上,,也可以解讀出許多資訊。從這個(gè)角度來看,,分配生員,、興辦學(xué)校確實(shí)是在前近代惡劣的技術(shù)條件下,對(duì)帝國(guó)對(duì)邊陲幾種不多的影響手段,。
游逸飛:里耶秦簡(jiǎn)里的先秦湘西“邊城”
接下來的兩場(chǎng)山城研究報(bào)告都偏向上古史的階段,。游逸飛關(guān)于湖南龍山里耶古城的研究十分重要,是因傳世文獻(xiàn)不足,、出土文獻(xiàn)稀少,,能以當(dāng)?shù)爻鐾恋暮?jiǎn)牘來研究秦漢城鎮(zhèn)的案例顯得尤其珍貴。湖南龍山里耶古城位于湖南西部,,是沈從文筆下一座典型的湘西邊城,,至今從長(zhǎng)沙出發(fā),還要坐上十幾個(gè)小時(shí)的大巴才能到達(dá),。它在秦漢是洞庭郡遷陵縣治所所在地,,兼負(fù)著湘西四大商鎮(zhèn)和秦代金、鐵,、錫開采礦城的功能,。從里耶秦簡(jiǎn)的斷簡(jiǎn)殘編里,游逸飛解讀出秦代遷陵縣有縣官三人,、人口一百九十余戶,、規(guī)模只有一座學(xué)校大小等資訊。以許宏的《先秦城市考古學(xué)研究》一書中對(duì)上古城市的分類來看,里耶古城雖只有一座軍事堡壘的大小配置,,卻承載了地區(qū)貿(mào)易集散的功能,。由于交通高度依賴水路,政令的到達(dá)十分緩慢,,地方官在行政處置上有很大的發(fā)揮空間,。在戶口收編的記載中,民族融合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苗人,、濮人被收并的現(xiàn)象很普遍。
城東北郊的墓地分布問題是以往報(bào)告人的研究焦點(diǎn),。如圖,,中央紅點(diǎn)為里耶古城,其東北綠點(diǎn)為麥荼戰(zhàn)國(guó)墓地,西南與清水坪西汗墓地隔水相望,考古發(fā)掘者認(rèn)為麥荼戰(zhàn)國(guó)墓地里有楚人,、苗蠻與濮人,清水坪西漢墓地內(nèi)有秦人,。游逸飛則認(rèn)為,麥荼墓地的時(shí)代可以延期至漢代,,它一直被使用,,只是埋在其中的族群隨時(shí)代有所輪替,它背后牽涉到政權(quán)轉(zhuǎn)換和人群轉(zhuǎn)移的大問題,,非常值得繼續(xù)探究,。另外,簡(jiǎn)牘中所記載的有關(guān)秦朝對(duì)外地人,、本地人的不同政策,,顯示出秦在統(tǒng)治六國(guó)故地順應(yīng)當(dāng)?shù)亓?xí)慣法、尊重傳統(tǒng)行政權(quán)力的傾向,,它很好地解釋了為何春秋以來到西漢結(jié)束的長(zhǎng)時(shí)段內(nèi),,里耶地區(qū)政權(quán)相對(duì)平穩(wěn)、叛亂稀少的歷史現(xiàn)象,。

(里耶地區(qū)墓地分布 游逸飛制)
黃川田修:山東歸城的上古巨型遺址令人驚嘆

(黃田川修在現(xiàn)場(chǎng) 沈雪晨攝)
最后一位學(xué)者黃川田修報(bào)告了他前兩年的研究《山東龍口歸城先秦城址——試讀早期中國(guó)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一文,。他是當(dāng)今以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的觀念來處理中國(guó)上古史問題的典型人士,。這篇文章的緣起是他2002年首次去山東龍口市考察,,目睹了西周至春秋遺留下來的歸城遺址,。作為一個(gè)日本人,,他被保存完好的高高夯土城墻震撼了,在西周時(shí)期,此地相較中原已是遙遠(yuǎn)的邊區(qū),,那為何出現(xiàn)這樣的大遺址呢,?
根據(jù)此地出土的青銅所具有的精致器型和良好材質(zhì)做出的考古學(xué)分析,黃川田修認(rèn)為歸城是上古時(shí)期中原王朝與北方夏家店文化交換青銅的重要流通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層時(shí)期,,遼河流域產(chǎn)生的銅、錫,、鋅向各地出口,,經(jīng)大連入渤海,在煙臺(tái)登陸,,過歸城入臨淄再輾轉(zhuǎn)流入今天的河南地區(qū),。由于歸城附近缺乏其他規(guī)模相當(dāng)?shù)倪z址群,也沒有出土任何規(guī)格高雅的青銅器,,因此他斷定歸城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很可能是從中原的華夏系統(tǒng)國(guó)家遷移過來的,外來的統(tǒng)治階層通過龐大的軍鎮(zhèn)建設(shè)和禮器配置對(duì)這一“非中國(guó)地區(qū)”進(jìn)行控制,,以此壟斷這里的交通和礦產(chǎn),。作為周王朝意志的體現(xiàn),歸城的案例證明上古時(shí)期的華夏系統(tǒng)國(guó)家的擴(kuò)張邊界,,黃川田修希望以此回應(yīng)日本學(xué)界提出的“中國(guó)早期王朝”概念中有關(guān)多元華夏文明起源的問題,,以及杜正勝提出的“城邦國(guó)家”概念之間的連結(jié)關(guān)系。

(日本東洋學(xué),、考古學(xué)專家今日設(shè)想的上古中國(guó)社會(huì)發(fā)展模式 黃川田修制)
筆者認(rèn)為,,以上兩位學(xué)者以較少的材料做了分析上古邊城形制、與中央關(guān)系的嘗試,,雖仍就一些具體歷史細(xì)節(jié)的還原上感到困難重重,,卻不忘回應(yīng)有關(guān)中國(guó)上古史的論述中最核心的大問題,十分值得肯定,。黃川田修還指出,,學(xué)者通過自己積累器物的類型學(xué)知識(shí)制作考古編年的方法,可以用以同文獻(xiàn)的記載互為對(duì)照,,以此在老問題上得出新的發(fā)現(xiàn),。相較起來,明清史研究的學(xué)者就顯得被繁浩的基層史料束縛了,,這樣不僅容易將歷史學(xué)研究的眼光局限于某一狹窄時(shí)間段和地域中,,陷于單一孤立的歷史案例,而忘記了對(duì)普遍性的,、大范圍內(nèi)的問題做出回應(yīng)的必要,,且容易忽略文獻(xiàn)以外的器物類型,、風(fēng)土民情所蘊(yùn)含的歷史信息,這樣一來,,即便走出了書齋,,目之所及仍不過是書,而無法進(jìn)入歷史學(xué)研究所真正需要的田野中去,。
會(huì)議心得:在田野中尋找歷史,?
在此次會(huì)議的總結(jié)部分,四人各自談了對(duì)此次研討會(huì)的感想,。他們都感到彼此研究的問題有所重疊,,均以帝國(guó)的邊陲——山城為切入點(diǎn),以此研究它與帝國(guó)中心的互動(dòng),。他們都受到了歷史人類學(xué)方法的影響,,所不同的只是關(guān)注的時(shí)代有所不同。以往的研討會(huì)常以斷代來劃分會(huì)場(chǎng),,研究不同歷史時(shí)段的學(xué)者無法交換意見,,因此能給予互相的啟發(fā)都相對(duì)有限。另外,,還有學(xué)者提出,,在研究云南、福建明代以后的情況時(shí),,歐洲人的旅行筆記亦是可以參考的史料,。
然而,此次會(huì)議在研究的方法和主題上雖稱得上時(shí)髦,,卻顯示出當(dāng)前歷史學(xué)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兩位明清史研究的學(xué)者為例,首先,,接觸大量的方志,、族譜等基層社會(huì)史料固然可以輔助還原過去重視不足的社會(huì)史變遷,卻容易忽略推動(dòng)古代歷史發(fā)展最重要的先導(dǎo)性因素——思想觀念,。盡管宋以后,,平民階層不斷崛起,文化大眾化傾向日趨顯著,,但古代社會(huì)的精英性格仍是基本不變的,。方志、族譜的編纂修訂者因缺乏與帝國(guó)精英的互動(dòng),,在地方或家族史的書寫中能夠呈現(xiàn)的帝國(guó)經(jīng)營(yíng)理念有限,,僅從這些文獻(xiàn)里,是不足以體會(huì)清朝何以要將帝國(guó)統(tǒng)治的觸角延伸至前朝從未涉及的地區(qū)的,。歷史學(xué)家將視角僅限于此,,便無法解讀出帝國(guó)在維持自身正統(tǒng)性,、擴(kuò)張疆域范圍、伸張?zhí)煜滦蛧?guó)家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的復(fù)雜考量,,也會(huì)與深受宋明理學(xué)熏陶的明清學(xué)者型官僚拉開距離,從而無法將區(qū)域的歷史進(jìn)程同帝國(guó)的演變發(fā)展做全面互動(dòng)的考量,。
其次是由此而來的,,在地方史研究中缺乏對(duì)歷史學(xué)理論架構(gòu)的回應(yīng),因之無法建立更具涵蓋性的解釋框架的問題,。比如像東川,、南屏這樣新興城市的開拓,對(duì)于施堅(jiān)雅(WilliamSkinner)以四川盆地為模型提出的傳統(tǒng)中華帝國(guó)六角形城市結(jié)構(gòu),,具有豐富的補(bǔ)充意義,。它們或深居內(nèi)陸,或遠(yuǎn)在邊疆,,或以傳統(tǒng)儒教手段整合,,或憑簡(jiǎn)單的軍政控制,并不能與周邊的都市群形成有效的往來,。它們?cè)诘蹏?guó)中處于何種位置,?發(fā)揮了怎樣的功效?在接下來的現(xiàn)代國(guó)家轉(zhuǎn)型面臨怎樣的處境,?這些都是可以注意卻沒有被充分討論的地方,。缺少了這些解釋框架,研究難免陷入瑣碎信息的采集,,或是對(duì)一個(gè)人們聞所未聞的山城進(jìn)行旅游簡(jiǎn)介的境地中去,。
最后是關(guān)于田野研究的方面。當(dāng)歷史人類學(xué)已經(jīng)成為一種時(shí)髦,,歷史學(xué)家下田野就不再是針對(duì)文獻(xiàn)材料不足時(shí)所作出的適當(dāng)補(bǔ)充,,而成為整個(gè)歷史學(xué)研究的先導(dǎo)性方法了。不得不說,,在學(xué)習(xí)他者語(yǔ)言,、深入掌握當(dāng)?shù)厝松钚螒B(tài)、建立一個(gè)異域社會(huì)完整模型的能力上,,歷史學(xué)家遠(yuǎn)不如正統(tǒng)人類學(xué)者,;在展現(xiàn)對(duì)人情世故的細(xì)膩觀察、表達(dá)對(duì)鄉(xiāng)土生活的深厚情懷上,,歷史學(xué)家又絕不像是文學(xué)作家一樣敏銳深刻,、洞悉人性。深入田野固然有很大的好處,,但當(dāng)它變成你用來說服對(duì)某一地區(qū)聞所未聞的人的唯一理由,,就顯得蒼白無力起來,。無論如何,對(duì)歷史學(xué)來說,,田野仍應(yīng)是一種補(bǔ)充和輔助,,否則就會(huì)喪失學(xué)科的最大優(yōu)勢(shì)——對(duì)史料的掌握和分析、對(duì)過去人群思想觀念的體認(rèn)和理解,。
(鳳凰歷史特約通訊員沈雪晨獨(dú)家報(bào)道)
所有評(píng)論僅代表網(wǎng)友意見,鳳凰網(wǎng)保持中立